敦煌所见于阗牛头山圣迹及瑞像
张小刚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内容摘要:敦煌壁画中的于阗牛头山圣迹及瑞像从盛唐开始出现,历中、晚唐,五代、宋,成为当时敦煌和于阗两地间交流的证明。关键词:敦煌;壁画;于阗;牛头山;瑞像
于阗牛头山,又称牛角山,是西域著名的佛教圣地,位于今新疆和阗西南噶喇喀什河畔乌加特之地。唐宋时期,敦煌壁画中出现了不少有关于阗的内容,其中就有牛头山圣迹及瑞像。孙修身先生曾对这些图像做过一些介绍和考证工作[1],笔者试图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莫高窟第345窟牛头山圣迹
在莫高窟第345窟甬道顶,绘有一铺于阗史迹画:画面中上部绘主尊,为一坐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座置于山顶平台上,山从画面中下部的海内升起,束腰,山下部为牛头形,两侧各跪四身神将。坐佛有圆形头光、身光,馒头形肉髻,圆脸,眉间有白毫,颈有三道,外着偏衫式袈裟,内着交领僧祗支,右手于胸前作说法印,左手置左膝,似作与愿印,顶有珠网形华盖,两侧各有双树,左右各坐三身弟子,均有圆形头光,双手合十,面朝主尊。画面上部南侧(主尊左侧)天空中绘三身较小的趺坐佛(中间一身略大),坐于束腰高台莲座上,驾云而来,云下存两身趺坐小千佛,下方地面上有荷叶、莲花,立一天王,有圆形头光,戴盔着甲,左手持戟,右手叉腰。画面上部北侧绘一天王与一弟子在水边合力作挖掘状,下方海面上星布千佛及莲花,存趺坐千佛九身,海边立一天王,有圆形头光,戴盔着甲,右手持戟,左手叉腰。画面中存榜题九方,均漫漶。画面下部已毁。画面大部分变色,呈灰褐色。(图1)

图1 莫高窟第345窟 于阗圣迹图
关于此铺图的时代,史苇湘等先生定在盛唐时期[2],王惠民先生修订《莫高窟内容总录》时改为五代[3],我们亲赴此窟考查后,认为无论从人物造型还是从绘画风格上看,均以盛唐较合适。此图内人物面相丰圆,身体壮实,尤其天王穿半臂,臂及腿扎行縢,着虎皮战裙的装束为唐前期武将常见形象;莫高窟五代时期现存壁画很少变色成灰褐色,而这对于唐前期的壁画则是常见的现象;主尊右下侧有几身千佛被后代用土红色重涂,有的土红色之下露底层的灰褐色,有的用土红色重描莲座后,与未经重描的身体部分相比较,明显比例失调,此土红色即甬道内五代边饰及垂幔之底色,在甬道北壁与顶的转交处还明显可以看出壁画的重层关系,因此我们认为此铺史迹画基本保持了盛唐时期的面貌。
我们认为图中表现的是于阗牛头山圣迹、瑞像故事。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2谓:
王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室餕伽山(唐言牛角)。山峰两起,岩隒四绝,于崖谷间建一伽蓝。其中佛像时烛光明。昔如来曾至此处,为诸天人略说法要,悬记此地当建国土,敬崇遗法,遵习大乘。牛角山岩有大石室,中有阿罗汉,入灭心定,待慈氏佛,数百年间,供养无替。近者崖崩,掩塞门径。国王兴兵欲除崩石,即黑蜂群飞,毒螫人众,以故至今石门不开。[4]
在唐代道宣所撰《释迦方志》卷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卷二十九中亦有类似记载[5],但文字较简略。《慧琳音义》卷十一“于阗”条下注曰:“其国界有牛头山,天神时来栖宅此山”[6]。《华严经》中有另一种说法,认为牛头山在疏勒(边夷)境内[7],澄观疏云:“然牛头山在今于阗国,此云地乳。佛灭百年方立此国,具如《西域记》,以集经之时未开,尚属疏勒故耳”[8]。玄奘所说“如来曾至此处,为诸天人略说法要,悬记此地当建国土,敬崇遗法,遵习大乘”的故事,可从《日藏经》与《西藏记》找到更详细的记载。
据隋代那连提耶舍译《日藏经·护塔品》记载,诸龙王受佛付嘱二十支提圣人处,其中,祇利呵婆达多龙王受付嘱守护供养的是阎浮提内于阗国中水河岸上牛头山边近河岸侧瞿摩婆罗香大圣人支提住处。当其他龙王都接收了佛付嘱的时候,祇利呵婆达多却提出了异议,于是如来对他进行了一番解释,兹移经文如下:
时祇利呵婆达多龙王即白佛言:‘世尊!如来今者以于阗国牛角峰山瞿摩娑罗乾陀牟尼大支提处,付嘱于我。然彼国土,城邑村落悉皆空旷,所有人民悉从他方余国土来,或余天下,或余剎中。菩萨摩诃萨、大辟支佛、大阿罗汉、得果沙门、五神通人,坐禅力故,向彼供养瞿摩娑罗,旧无众生,一切来者,皆是他国。世尊!此二十八诸夜叉将,不肯护持我。今怪此,所以者何?以彼不护,我等诸龙得于恶名。’佛言:‘龙王莫如是说。何以故?今有二万大福德人见于四谛,从沙勒国而往彼住,以彼二万福德众生有大力故,于此瞿摩娑罗香山大支提处,日夜常来一切供养。龙王当知,如是之时,恒不饥乏。又迦叶佛时,彼于阗国名迦逻沙摩,国土广大,安隐丰乐,种种华果,众生受用。彼国多有百千五通圣人,世间福田,依止其中,系念坐禅,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其国土安隐丰乐,彼土众生,多行放逸,贪着五欲;谤毁圣人,为作恶名;以灰尘土,坌彼圣人。时诸行者,受斯辱已,各离彼国,散向余方。时彼众生,见圣人去,心大欢喜。是因缘故,彼国土中,水天、火天皆生瞋忿,所有诸水,河、池、泉、井一切枯竭。时彼众生,无水火故,饥渴皆死。是时国土自然丘荒。’佛告龙王:‘我今不久往瞿摩娑罗牟尼住处,结加七日,受解脱乐。令于阗国于我灭度后一百年,是时彼国还复兴立,多饶城邑、郡县、村落,人民炽盛,皆乐大乘,安隐快乐,种种饮食及诸果华,无所乏少。’时僧儿耶大夜叉将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佛言:‘大夜叉将!汝忆过去,久远事不?’僧儿耶言:‘我念往昔迦叶佛时,此牛角山圣人住处,迦叶如来亦于彼处,七日结加,受解脱乐。过七日已,从禅定起。我时到彼瞿摩娑罗香牢尼住处,礼拜供养。彼迦叶佛,亦以平等法行比丘,精勤方便,坐禅正慧,修善法者付嘱于我。’时祇利呵婆达多龙王白佛言:“世尊!我誓于此瞿摩娑罗香大支提所,常护不舍。乃至佛诸弟子法行比丘,精勤修善,不受畜者,我等守护,乃至法尽,或水或火,或龙、夜叉,或鸠盘茶。弥勒佛时,瞋忿作恶,如是时中,非我所护。’佛言:‘善哉!善哉!龙王,若能如是发至诚心,加护我法,住持法母,令法久住,是我真伴,是好檀越。”[9]
又据《西藏记》记载:迦叶佛(Kacyapa)之时,仙人(Rishis)虽已来此国,然国人颇冷遇之,因此,触龙族(Nagas)之怒,而变此干燥之国为一大湖。释迦牟尼佛遂率其众弟子来临此国,以光明覆照此湖。其光有三百六十三─—Thomas氏改此数为三百五十三,谓此数为其后此国建立寺院之数─—道光芒,集中于睡莲之处。光芒既经统一,乃左右绕湖之周围三次而没水中。斯时,佛命舍利弗(Cariputra)以其杖端,又命毗沙门(Vaicravana)以其锐枪突刺此湖。于是佛住瞿室餕伽(Gosirsa)山对阿难(Anna)曰:自此以后,湖将干涸,我灭度后,此地可称为Li-Yul,光芒三次所绕之处,可呼为U-then,建设都城,城中有五塔。此为佛之豫言。[10]
以上两文献的记载不尽相同,所云曾经降临的灾难更是两个相反的极端,其结果一个是诸水枯竭,另一个则是变干燥之国为大湖。两者相似之处在于都提到佛来到牛头山,并对此地“当建国土,敬崇遗法”作了预言。莫高窟第345窟甬道顶于阗史迹画中的内容,可以从《西藏记》的记载中得到较契合的解释。画面中部是释迦牟尼在牛头山为诸弟子、天龙神将等说法,画中天王就是北方毗沙门,上部北侧为舍利弗持锡杖,毗沙门持戟合力刺穿海底,放出海水,此即“舍利弗、毗沙门决海故事”。这个故事在敦煌所出藏文文献P.t.960《于阗教法史》(Li-yul-chos-kyi-lo-rgyus)中也有记载:
当于田地方还是海子时,世尊命令北方天毗庐舍摩那和比丘舍利子二人说;‘目前的这个海子地方,是三世佛另外一个世界,以后将成为人众居住的处所。现在生长莲花之处,以后将成为一座座寺院,会出现许多菩萨。你去把海子淘净,使它以后成为人众居住的地方吧!’北方天王和舍利子二者到盛崑山用锡杖的下端和矛的尖端把海底刺穿,海水流干了,于是,成了人能居住的地方。此时,正是佛涅槃一百年的时光。[11]
《于阗教法史》中的北方天王“毗庐舍摩那”即毗沙门,比丘“舍利子”亦即舍利弗。变海为陆的决海故事画,除第345窟外,还出现于莫高窟第231、237、236、53窟主室龛内北披,第9、39、45、146、334、340、397、401、454窟甬道顶,第85窟甬道北披(残),第144窟前室北壁龛上,第220窟南壁(编者:见段末注),榆林窟第32窟东壁、第33窟南壁。莫高窟第25、98、100、108、126、342等窟原来也应曾有绘制,今已毁。在莫高窟第231、237窟内毗沙门、舍利弗上方还绘有一方城,即预言中的于阗都城(图2)。莫高窟第220窟与第345窟相似,除了与舍利弗相对的毗沙门外,天王还现身于海内其他几处,而且第220窟在大海与牛头山之间也绘有两座城。在绝大多数洞窟内,此故事画都处于史迹画及瑞像群中,和其它瑞像、圣迹等共存,但也有例外,除了莫高窟第345窟于阗史迹画具有一定独立性外,第144窟前室北壁龛上的小画面是单独出现的,在榆林窟第32窟内则出现在东壁《普贤变》内,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此种瑞像有时单独出现在壁画中,而不与其它非于阗的圣迹或瑞像甚至不与其它瑞像同时出现,说明了它在于阗诸瑞像中的特殊地位,或者说它是具有标识于阗作用的瑞像,这可能与它反映了于阗此地方形成的故事有关。关于此故事画,敦煌“瑞像记”中有文字记录:“于闐國舍利弗毗沙門天王决海時”(P.3352),“舍利弗共毗沙門神决海至于闐國”(S.2113A),壁画中有的还存有榜题,如“于闐國舍利弗毗/沙門天王决海時”(第231窟),“于闐國舍利弗毗沙門/天王决海時”(第237窟),“舍利弗决海時”(第53窟)、“北方眾□天王決海至于闐國”(第220窟)等。
(注:第220窟主室南壁瑞像群今已不存,伯希和、罗寄梅曾摄有照片,伯希和还记录了部分榜题。)

图2 莫高窟第231窟 毗沙门舍利弗决海故事画
除了榆林窟第32窟东壁《普贤变》内的牛头山外,敦煌出现的其余牛头山图都和牛头山瑞像组合绘制在一起,一般为山顶画结跏趺坐佛像,下方为牛头形山岩,牛头额上或嘴内伸出阶梯,有些梯上还有攀爬的人,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天梯。天梯意即能凭之登而升天的梯子,常与高山联系在一起,如唐代湛然撰《止观辅行传弘决》云:“(天台山)本名天梯,谓其山高可登而升仙”[12]。印度有天梯圣迹,智猛法师在迦维罗卫国“其所游践,究观灵变,天梯、龙池之事,不可胜数”[13],玄奘西游时也曾“重礼天梯圣迹”[14]。《于田教法史》谓:“金刚手密教之主,现居于牛头山的阶梯山顶雄甲”[15],可见牛头山有似天梯一类的阶梯。关于牛头山圣迹,敦煌“瑞像记”中有文字:“于闐牛頭山,此是于闐國”(S.5659),“于闐牛頭山”(S.2113A)
二、两种牛头山瑞像
敦煌壁画中有两种牛头山瑞像。一种是上文提到的置于牛头山顶的坐佛像,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右手作说法印,见于莫高窟第9、25、39、45、85、98、108、126(残)、146、220、334、340、342(熏黒)、345、397、401、454、449等窟,榆林窟第33窟内。孙修身先生曾定此坐佛瑞像为迦叶佛[16],笔者以为应为释迦牟尼像,表现的是释迦在牛头山顶结跏趺坐向八部众说法,即“昔如来曾至此处,为诸天人略说法要,悬记此地当建国土,敬崇遗法,遵习大乘”、“(佛告龙王)我今不久往瞿摩娑罗牟尼住处,结加七日,受解脱乐”的场景。
在大多数洞窟内,此瑞像均处在经变式的瑞像、圣迹群图中,而且占据了整铺图最显著的中间位置。在莫高窟第25、454窟、榆林窟第33窟内,此瑞像还身处殿阁中,是表现佛在牛头山伽蓝里。与第345窟内相似,第220窟此瑞像左右各有一弟子,两侧空中各驾云飞来三身小千佛,牛头山山腰两侧有龙、天等。第454窟牛头山伽蓝场景内,不但驾云飞来成对的菩萨,整齐排列塔与比丘,而且在展开的双层楼的每间房内各有一身小立佛。敦煌所出法成汉译本《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P.2139)谓:
于阗塔寺,五百菩萨常护持,故二百五十以出家仪,二百五十在于俗徒,受生护持。牛头山寺,贤劫一千五佛,常当履践,以为宫殿。为诸贤圣威德慈悲加持于阗塔寺妙法,故行法人多于余国,久住于世。[17]
可见,第345、220窟飞来的小千佛,第454窟各房间内的小立佛就是贤劫千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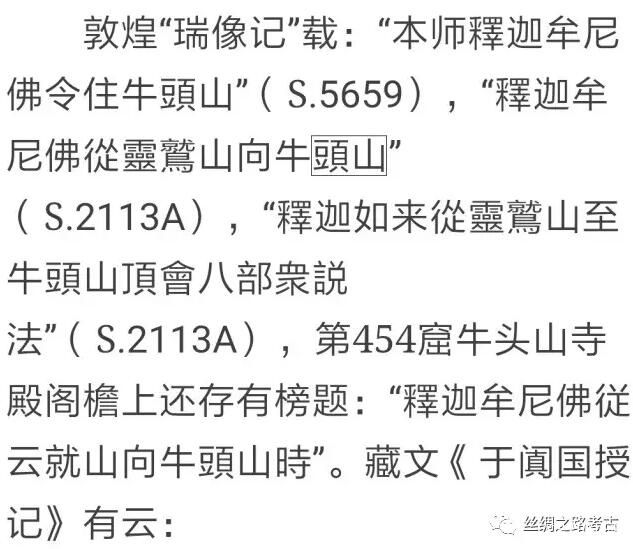
尔时于阗久为湖泊,释迦牟尼佛为预言:该湖泊将成陆地获治国家,乃引菩萨、声闻弟子在内之二十万众,龙王、天人等八部众於灵鹫山升空。既至于阗,时为湖泊,乃坐於今mgo-ma河附近水中莲花坐上。释迦预言该湖泊将变为获治之陆地之国,乃口申教敕,命包括八大菩萨在内之二万随侍、三万五千五百○七眷属护法神祗护持该国的这一供养圣地。舍利弗、毗沙门奉敕而开通墨水山,排除湖水,而得地基。佛於原来莲花座上,在牛头山现今立有释迦牟尼大佛像处结跏七日,而后返回天竺国之吠舍厘城。[18]
由此可知,为于阗作预言的佛为释迦,命毗沙门、舍利弗决海的佛为释迦,引领菩萨、声闻(弟子)、天龙八部在牛头山顶结跏趺坐说法的佛也为释迦,因此敦煌壁画中坐于牛头山顶的佛像无疑当是释迦瑞像,上述敦煌“瑞像记”的文字应该就是针对此种瑞像。
需要说明的是,莫高窟第449窟主室龛内北披东起第一格与第85窟甬道北披西起第七格内所绘瑞像,过去无人提及,经笔者反复辨识,结跏趺坐佛座下均有牛头形山峰,也应属于牛头山瑞像。(图3)与其它同类图像不同的是,它们处于逐个绘瑞像的方格中,而不是位于经变式的瑞像、圣迹群图中。第449窟龛内的瑞像图虽经宋代重新涂彩,但其内容未变,仍为中唐原作,第85窟由都僧统翟法荣建于公元862—867年之间,属敦煌晚唐早期,经变式的瑞像、圣迹群图则可能最早出现在晚唐晚期,流行于五代宋时期,所以上述两种结构在时代上应有一定衔接关系,也就是说,对瑞像群的表现形式即构图布局等方面,在晚唐时期曾出现过一个转变。

图3 莫高窟第85窟 牛头山瑞像
敦煌壁画中还有另一种形式的牛头山瑞像,形象为一身立佛,多站在莲台上,有华盖、圆形头光,有的有椭圆形身光,身体与所着袈裟一色,或淡青或浅蓝色,左手垂于体侧,手把袈裟一角,右手于右胸前作说法印,今见于莫高窟第231、237、72等窟主室龛内。此瑞像在第231窟位于龛内南披东起第7格内,有题榜两方:“此牛頭山像從耆山履”、“空而来”,东邻“中天竺摩诃菩提寺造释迦瑞像”,西邻“指日月像”;其在第237窟位置与在第231窟相同,榜题为“此牛頭山像從耆山履空而/来”(图4)。第72窟龛内南披东起第4格内绘一立佛瑞像,着土红色袈裟,左手下把袈裟,右手作说法印,有榜题:“南无聖容像来住牛頭山”,同披第6格内瑞像姿势与其相同,但身衣一色,均为浅蓝色,榜题:“南无聖容諸像来住山”,西披南起第2格内瑞像亦题:“南无聖容諸像来住山”,但这一身左手于胸前把袈裟,右臂及手直垂体侧,据形象不难辨识为凉州瑞像。南披的两身中,参照第231、237窟瑞像形象,尤其身体及袈裟颜色情况,我们判定第6格内立佛可能是牛头山瑞像,但第4格内榜题清晰,与左右相邻两格内瑞像也不存在题写错位的现象,仅在身色上与其它相同题材的像不一致,故只能存疑。按耆山即耆阇崛山,意译作灵鹫山。根据洞窟内的榜题,我们知道这种形式的瑞像,仍与释迦牟尼从灵鹫山来牛头山说法故事有关,然而,与前一种表现说法场景的释迦趺坐瑞像不同,此种瑞像表现的是释迦“履空而来”的形象,所以绘成立像就不难理解了,而上引《于阗国授记》文有云“在牛头山现今立有释迦牟尼大佛像”,立瑞像可能就是以立在牛头山的一身释迦大佛像为依据而绘制的。

图4 莫高窟第237窟 牛头山瑞像
牛头山瑞像中前一种坐像出现在莫高窟盛唐第345窟的甬道顶部,中唐第449窟的主室龛内,晚唐前段第85窟的甬道北披,晚唐后段第340、9窟的甬道顶,五代第39、45、98、108、126、146、334、342、397、401窟的甬道顶,宋代第25、454窟的甬道顶与第220窟的主室南壁,榆林窟五代第33窟的主室南壁。后一种立像只出现在莫高窟中唐第231、237窟,晚唐初期第72窟的主室龛内。可见,两种瑞像中以前者较为流行,历盛唐至宋初约三百年,在归义军时期洞窟中还位于经变式瑞像群图的中心,而后者仅在九世纪中期流行一时。
另外,在经变式的瑞像、圣迹群图中牛头山坐瑞像正上方均绘有一身立佛瑞像,背靠山岩,绝大多数左手把袈裟,右臂垂于体侧(少数两手于胸前作说法印),从图像上看,它们明显是“凉州瑞像”,表现的是此瑞像身处裂开之山间的场景。孙修身先生误定其为牛头山立瑞像[19],将其与牛头山坐瑞像当作了一个故事的两个情节,在这里需要特别地指出来。在中唐时期的第231、237等窟内,凉州瑞像位于龛内东披的中心(图5),与西披中心的分身瑞像(双头佛像)相对,苏远鸣认为分身像“位于荣誉位置上”[20],那么凉州瑞像被安排在对应位置上,可能也显示了其较重要的地位,晚唐以后它与牛头山坐瑞像一起绘在经变式瑞像、圣迹群图的中心位置,更是加强了这种特殊的意义,总之,我们认为处于经变式瑞像、圣迹群图中最显著位置的,是牛头山坐瑞像和凉州瑞像两种瑞像(图6),而不是过去认为的只有一种牛头山瑞像,由此我们对整铺经变式瑞像、圣迹群图又有了新的认识,即虽然牛头山瑞像在其中有较重要的地位,但它并不是作为整铺图像的主尊出现的,而且图中还分布着古印度、西域、河西及中原各地的诸多瑞像、圣迹故事,所以过去有人把这种经变式瑞像、圣迹群图称为于阗史迹画是欠妥当的。

图5 莫高窟第237窟 凉州瑞像

图6 莫高窟第454窟 牛头山瑞像与凉州瑞像
三、图像反映的若干历史问题
除了出现在瑞像群中的牛头山瑞像外,莫高窟第345窟与榆林窟第32窟内的牛头山圣迹或瑞像基本上是单独出现的。它们虽显零星,却更能反映出于阗和敦煌两地间的紧密联系,尤其是直接的交往关系。
众所周知,唐初设安西四镇,又几经弃置,7世纪末西域被反复争夺的局面才结束,唐朝在西域的稳定统治一直持续到八世纪末叶。莫高窟第345窟的牛头山圣迹是敦煌石窟中现存最早的有关于阗的史迹画,反映了盛唐时期于阗和敦煌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
吐蕃统治敦煌的中唐时期,于阗亦被其占领,于阗瑞像开始大量出现在洞窟中。中唐早期的莫高窟第154窟内绘有于阗建国传说,中唐晚期前段的莫高窟第144窟绘有单独的决海画面,中唐晚期的莫高窟第231、237、236及53等窟内各地瑞像成群出现,其中就有多种于阗瑞像。单独的图像可能是两个地方之间直接交流的证明,而瑞像群的出现应该跟超越地方的行政力量即吐蕃的统治有关,换言之,对古印度、西域、河西及中原等地各种瑞像的整合工作,没有出现在唐朝控制西域与河西的盛唐时期,而出现在吐蕃统治这些区域的中唐时期,反映了吐蕃对佛教的重视程度以及此时期吐蕃对外来文化的汲取与整理。
中唐晚期的瑞像图多位于龛内的方格中,归义军时期则主要在甬道顶采用经变式与方格式结合的形式(曹氏时期少数出现在主室壁面上),不仅反映了对传统的继承,并且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归义军张氏、曹氏政权与于阗李氏王国的关系问题,多有学者论述,已经基本清楚,此不赘言,敦煌石窟内出现的于阗供养人像与瑞像图是两地间密切交往的图像学证明。
最后补充说明一点,榆林窟五代第32窟内的牛头山(山顶无瑞像)与毗沙门、舍利弗决海等场景绘在东壁门北的《普贤变》中,这有点令人奇怪,但如果我们将东壁门南的《文殊变》结合起来看,就不难理解了。此《文殊变》属新样文殊图,主尊坐骑狮子由于阗国王牵拽,云中化现菩萨、罗汉、天人等,周围山水连绵,其中星布寺院、庙塔、金桥等,主尊下方有狮子化现处,文殊现老人点化佛陀波利处等场景,说明文殊身处五台山道场内。《普贤变》中主尊周围也绘山水,其间星布寺院、庙塔等,图中出现的牛头山与决海场景表明了普贤正处在于阗境内,而非其道场峨嵋山。我们认为如此处理并非偶然,而是为了突出于阗的佛教地位。五台山与牛头山均为佛教圣地,一东一西常为信徒巡礼,S.6551V《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是一位高僧于五代中叶在西州回鹘讲经用的文本,讲经文的开头部分述说了这位僧人游方的行迹:
但少(小)僧生逢浊世,滥处僧伦,全无学解之能,虚受人天信施,东游唐国幸(华)都,圣君赏紫,丞(承)恩特加师号。拟五台山上,松攀(攀松)竹以经行;文殊殿前,献香花而度日。欲思普化,爰别中幸(华),负一锡以西来,途经数载;制三衣于沙碛,远达昆岗。亲牛头山,巡于阗国。更欲西登雪岭,亲诣灵山,自嗟业鄣(障)尤深,身逢病疾。遂乃远持微德,来达此方,睹我圣天可汗大回鹘国,莫不地宽万里,境广千山,国大兵多,人强马状。
因此,将五台山与牛头山对称绘制亦无不可。文殊和普贤还是守护于阗的八大菩萨中的两位,据敦煌藏文《于田教法史》记载:
八位天生的菩萨,现在还在于田,他们的名字是:金刚手密教之主,现居于牛头山的阶梯山顶雄甲。观世音居于菊年。虚空藏居于桂仲。文殊和牟尼巴瓦二者居于牛头山,地藏王居于卓帝尔。普贤居于多雷僧伽保陇。药师王居于马诺觉。弥勒菩萨居于麦诺聂。[21]
敦煌于阗语卷子P.2893称:
尔后八部菩萨取其国,居于各有所依的住地(寺庙)之区,以造福众生;彼(释迦?)为众生福祉而来Bisinana村(?),大加称许。药师住Banacva(或Banaca),普贤居Ttula之Sagapalam,地藏住nanagirai,观世音救护众生于Jusna,文殊及其眷属居迦叶佛舍利堂,摩尼跋婆居……,虚空藏为护持养育众生住萨迦耶山谷……八护法者威力强大,现形庇护周围之地。[22]
所以,将普贤绘在于阗境内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总之,绘者使此窟文殊、普贤图内均出现于阗的因素,明显是为了突出于阗的佛教地位,从而反映出这个时期敦煌和于阗之间良好的关系。
注释:
[1] 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介绍(三)》,载《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孙修身主编《佛教东传故事画卷》第83~100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9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有简体字版)。
[2]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第127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11月。
[3]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第141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12月。
[4] [唐]玄奘、辡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下)》第1013~1014页,中华书局,2000年4月。
[5] [唐]道宣撰《释迦方志》,见《大正藏》第51册第951页;[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二)》第889页,中华书局,2003年12月。
[6] [唐]慧琳撰《一切经音义》,见《大正藏》第54册第375页。
[7] 《大正藏》第9册第590页,第10册第241页。
[8] [唐]澄观撰《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四十七,见《大正藏》第35册第860页。
[9] 收入《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五,见《大正藏》第13册第294~295页。
[10] 参见[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第140~141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
[11]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第148~149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8月。
[12] [唐]湛然撰《止观辅行传弘决》卷一,见《大正藏》第46册第149页。
[13]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125~126页,中华书局,1992年10月;[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第580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
[14] [唐]慧立本、彦悰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见《大正藏》第50册第249页。
[15] 前引王尧、陈践书第151页。
[16] 前引孙修身书图版54、78。
[17] 收入《大正藏》第51册第996页。
[18] 转引自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文(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2月;又收入同作者著《于阗史丛考》第212~279页,上海书店,1993年12月),原文见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第一卷》(伦敦,1935年)第89~90页与恩默瑞克《关于于阗的藏文文献》(伦敦,1967年)第2~5页。笔者未能见后两书。
[19] 前引孙修身书图版70、77。
[20] [法]苏远鸣(Michel Soymie)著,耿昇译《敦煌石窟中的瑞像图》,见《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第151~175页,中华书局,1993年12月。
[21] 前引王尧、陈践书第151页。
[22] 转引自张广达、荣新江前引文,原文见贝利《于阗语杂考》(Hvatanica)(BSOS)四,《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学报》第十卷,第4期,1942年,第892页。
编者按:本文原载《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第6-11,115页。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钱雨琨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投稿邮箱:feiwen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