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春雷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长期以来,珠饰作为国内考古发掘中获得的一大类材料,一直未能受到足够重视和系统研究。珠饰这类材料,个体细小琐碎,很容易被忽略。琐碎细小的珠饰,研究起来其实并不容易,根据珠饰的材质、颜色、大小、形状、制作工艺(包括改性工艺、成型工艺、钻孔工艺和装饰工艺等)、外观纹饰等可以细分为很多种类。珠饰的年代、地域、文化属性和用途,以及其包含的交易和交流信息,反映的一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有其他与民族学和人类学相关的内容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来收集整理,并结合发掘材料、馆藏资料、历史文献和流传信息等,运用一些特定的科技分析方法,才能得以揭示。所以,珠饰研究需要多学科的跨领域协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很难获得系统性的成果。在珠饰研究方面,国外很多学者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使我们得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开展工作,如英国的霍勒斯·贝克(Horace C. Beck)[1]、伊恩·葛鲁夫(Ian C. Glover)[2]、伊莉莎白·莫尔(Moore. E)[3]、圣乔治·辛普森(St John Simpson)[4]、穆雷(P.R.S. Moorey)[5]、芭比·坎贝尔·科尔(Barbie Campbell Cole)[6],法国的贝伦尼斯·贝丽娜(Berenice Bellina)[7],美国的乔纳森·马克·科诺耶尔(Jonathan M. Kenoyer)[8]、罗伯特·刘(Robert K Liu)[9]、小彼得·弗朗西斯(Peter Francis, Jr.)[10]、路易斯·杜宾(Lois Sherr Dubin)[11]、詹姆斯·兰克顿(James Lankton)[12]、吉米·艾伦(Jamey D. Allen)[13]等。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英国攻读考古学博士期间,即开始研究珠饰。夏鼐先生的博士论文就是《埃及的古代珠饰》(Ancient Egyptian Beads)[14],回国以后还偶有珠饰方面的文章发表[15]。近年来,国内考古学家和科技工作者逐渐开始关注珠饰研究,并发表一些学术专著和研究文章[16],这是很好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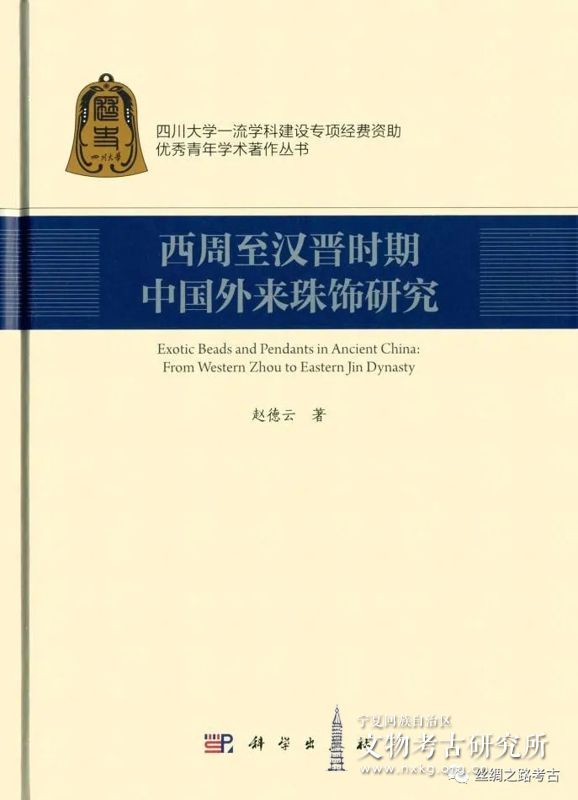
2016年4月赵德云先生出版《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作者在开篇内容提要中,讲述了自己的写作构思:“主要着眼于西周至汉晋时期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珠饰种类,通过观察他们各自母型在传播过程中的形态及使用功能的变异,研究外来文化因素的调适机制;并通过分析外来珠饰传播的可能中介者,勾勒其传播的途径,结合不同种类珠饰流行时代的分析以及流行地域等情况,以其时欧亚大陆的宏观历史背景为参照,总结西周至汉晋时期外来珠饰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特征”。
全书包括四个章节。在结语中对全书内容进行回顾和总结。最后附上十个附表,列举书中涉及珠饰资料的发掘出处。
第一章题为“引论”,主要介绍该书研究的珠饰材料的界定范围、珠饰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价值、珠饰的分类和描述、国内外珠饰发现与研究回顾、珠饰的研究方法和珠饰研究的难点。
第二章题为“西周至汉晋时期的外来珠饰”,分十一节梳理了十三类珠饰,分别是费昂斯珠、钠钙玻璃珠、蜻蜓眼式玻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印度-太平洋珠、琥珀珠、多面金珠、壶形珠、辟邪形珠、装金玻璃珠、人面纹珠、青金石珠和人头坠子。作者主要列举了以上十三类珠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现情况,这些珠饰可能的来源,以及中国发现的这些珠饰与域外相关地区可能存在的联系。
第三章题为“模仿与变异:珠饰反映的中国文化对外来事物的调适机制”,主要论述中外珠饰制造材料和使用传统的差异、中国珠饰制造中对外来珠饰的模仿、外来珠饰进入中国后的变异。最后一节,作者阐述自己的观点,珠饰反映的中国文化对外来食物的调适机制:“即撞击-吸收-改造-融合-同化的过程”。
第四章题为“珠饰反映的西周至汉晋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特征”。作者试图通过书中涉及的13类珠饰的种类、输入路线、输入动因及中介者等几个方面的变化,考察西周至汉晋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特征。
作者从大量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材料中,摘选出可能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的西周至汉晋时期的十多类珠饰,其工作量可想而知。这为其他学者研究这时期的珠饰提供了很多参考。作者在这些珠饰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外来珠饰进入中国以后,引起的本土工匠模仿和工艺技术上的革新。最后,作者试图从外来珠饰输入中国的路线等因素的变化,研究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特点。从珠饰角度研究古代文化交流,在国外已经有很多实践,但是在中国考古学界还不多见,研究基础相对薄弱。赵德云先生迎难而上,实属可贵。
不过,赵德云先生书中也有一些内容值得商榷,大致如下:
有关选题年代跨度的问题。作者选择研究珠饰年代起点为西周,书中第7页写的理由是“从目前的珠饰考古材料观察,外来珠饰在中国的出现或是中国珠饰制造中受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最早的年代是在西周。因此我们以西周时期作为研究的起始年代”。实际上,目前中国珠饰考古材料中,至少有一类材料无论在出土数量、地域范围和年代跨度上都很大,与外来文化因素关联非常密切,而且在随后近四千年中,占中国珠饰的比重都比较大,其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年代要远早于西周,这种珠饰就是红玛瑙珠和红玉髓珠(后统称红玉髓珠)。红玛瑙和红玉髓无论在矿物来源、物化属性、颜色、制作工艺等都非常接近。事实上红玛瑙和红玉髓是紧密生长在一起的矿物[17]。红玉髓珠广泛被发现于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和中亚地区的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晚期的遗址中[18],而红玉髓珠在中国出现大约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图1),一直到商晚期妇好墓依然有出土[19]。从西周开始,红玉髓珠的数量较之前大大增加[20],所以红玉髓珠是中国古代珠饰中,与外来文化影响非常紧密的一种考古材料。

图1:新疆昭苏县卡拉苏乡出土印度河谷文明时期蚀花红玉髓珠、青金石珠等钏饰(采自覃春雷《新疆发现印度河谷时期蚀花红玉髓珠的考古意义》)
作者书中第8页有关界定“中国”与“外来”的概念时,选用“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作为其书中“中国”内涵的定义,对应的此“疆域”以外的地区为“外来”。在论及中外文化交流时,用此疆域界定,无可厚非。作者书中使用“国外珠饰”(如138页、146页)、“外来珠饰”(如149页、150页、153页、162页、169页、171页)等词界定外来珠饰,同时又用“西方珠饰”(如142页)、“西方”(如143页、149页)、“西方世界”(如139页)“中西文化交流”(如179页、222页)等概念,论述与外来珠饰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相关内容。在作者为本书设定的“中国”与“外来”概念前提下,“国外珠饰”可以等同于“外来珠饰”,但是不能等同于“西方珠饰”、“西方”(珠饰)、“西方世界”珠饰。“西方珠饰”、“西方”、“西方世界”、“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西”亦需要提前界定,指代的外来文化范围,例如可能包括“中国”以西的两河流域、伊朗、希腊罗马、埃及、地中海东、叙利亚、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文明、古印度、中亚等;那么蒙古高原以北的西伯利亚地区,“中国”以南的东南亚,“中国”东的日本、韩国,应该都不在“西方”的范围,这些区域进入“中国”的珠饰,亦不在作者讨论的“中西文化交流”内容中。实际上,汉晋时期,有大量来自东南亚(越南、泰国、缅甸等地)的外来珠饰经由还海上丝绸之路网进入中国。在广西合浦、广东徐闻、云南滇文化遗址(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湖南汉晋时期遗址等,都出土了大量各种材质的外来珠饰,现在展出于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长沙市博物馆等。所以在“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语境下,“外来”与“西方”不能等同,“中外文化交流”与“中西文化交流”亦不能等同。
作者书中涉及的13类珠饰的分类方法问题。第13页中,作者承认“按照考古工作的一般习惯,在对出土遗物进行类别划分时,或依器物的材质,或依器物用途,前一种办法较为通行”,这也是夏鼐先生在《田野考古方法》中所倡导的。但是作者书中讨论的13类珠饰,并未采用材质或用途的基本分类法。其实,在研究珠饰时,通常的分类包括材质、用途、工艺、外观特征、地域、商品名或通俗名等,科学且系统,便于梳理,避免交叉和遗漏,也方便比较和讨论。例如按笔者以上所提到分类方法梳理,作者书中讨论的13类珠饰的细分情况如下:
(一)人造材质类:费昂斯珠(二级分类按工艺)、钠钙玻璃珠(二级分类按化学成分)、蜻蜓眼式玻璃珠(二级分类按外观特征)、印度-太平洋珠(二级分类按分布地区和来源)、装金玻璃珠(二级分类按工艺)、人面纹珠(二级分类按外观)、“人头坠子”(二级分类按外观)。
(二)无机材质类:青金石珠(二级分类按材质)、“蚀花肉红石髓珠”(二级分类按材质和工艺)。
(三)有机材质类:辟邪形琥珀珠(二级分类按材质:外观。第123页,作者列举的大部分国内出土辟邪形珠的材料为琥珀,其他材质的辟邪形珠可以兼作讨论,就像作者书中讨论琥珀珠时,亦把辟邪形琥珀珠兼作讨论一样)、其他形状琥珀珠(二级分类按外观,为辟邪形之外的其他形状的琥珀珠饰)。
(四)金属材质类:多面金珠(二级分类按材质和外形)、壶形珠(二级分类按材质和外形。第119页,作者列举和讨论的国内出土壶形珠绝大部分为金属,如有非金属材质壶形珠可以兼论)。
这样将珠饰研究材料进行梳理,系统且清楚,研究材料重叠较少,可以较好发现遗漏和问题,也便于开展后续的研究。
例如,(一)人造材质类珠饰中,除了现代才出现的塑料珠饰,基本是硅酸盐熔融或部分熔融反应产物(费昂斯和玻璃等都属于此类)。梳理作者所讨论的珠饰内容,可见还缺少国内考古出土的马赛克玻璃珠(如广西贵县铁路卫生所出土,作者分类中的人面纹珠也属于此类)、缠丝纹玻璃珠(如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和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的缠丝纹玻璃珠)等。
(二)无机材料类珠饰中,很容易发现作者遗漏了很多外来珠饰和与外来文化相关珠饰,如红玛瑙珠、水晶珠、紫水晶珠、石榴子石珠、绿柱石珠(如海蓝宝石珠)、缠丝纹玛瑙珠等。
(三)有机材质类珠饰中,除两种琥珀珠饰外,煤晶珠饰、珍珠珠饰、珊瑚珠饰、海贝珠饰等,这些外来珠饰和可能与外来文化相关有机材质珠饰,作者亦未进行研究讨论。
(四)金属材质类珠饰,作者书中讨论了多面金珠。但还有如作者书中第116页与多面金珠一同出土的橄榄形和多双锥形金珠等,这些外来珠饰或可能与外来文化相关金属材质珠饰,作者书中亦未讨论。
可见作者书中对很多中国考古出土的外来珠饰或与外来文化有关的珠饰的梳理和研究还很不充分。例如作者书中讨论的西周至汉晋时期的外来珠饰,有关材料整理工作依然有很多不足。例如新疆(如楼兰、尼雅、山普拉等遗址)(图2)、青海(如上孙家寨)、西藏(如故如甲木和曲塔墓地)、甘肃(如干骨崖、火烧沟、马家塬等遗址)(图3)、广西(如贵县、合浦等地汉代遗址)、湖南(如长沙曹[女巽]墓等)、云南(如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等滇文化遗址)等地区出土了大量外来珠饰和与外来文化有关的珠饰,其中部分外来珠饰或与外来文化有关的重要珠饰类型,亦未能被全面的纳入作者书中的讨论,这是作者书中有关中国古代珠饰研究的一些局限。这些局限亦会导致作者书中对外来珠饰投射的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易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

图2: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红玉髓珠、绿松石珠等钏饰(采自《玉门文物》)

图3:新疆若羌楼兰古城出土汉晋时期红玉髓珠、玻璃珠等钏饰、项饰(采自《中国西域·丝路传奇》)
作者在书中讨论的13类珠饰,实际上采用的是穷举法,结果既未能“穷”尽其珠,亦“举”得不够。作者书中讨论的珠饰材料交叉重叠,细看分类标准非常混乱。作者书中讨论的13类珠饰在一级分类时涉及至少六种互相交叉重叠的分类标准,如纯材质分类(青金石珠、琥珀珠)、化学成分分类(钠钙玻璃珠)、材质和工艺分类(费昂斯珠、装金玻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材质和外观特征分类(蜻蜓眼式玻璃珠、多面金珠)、外观特征分类(壶形珠、辟邪形珠、人面纹珠、人头坠子)、材质和地域特征分类(印度-太平洋珠)。作者书中讨论的13种珠饰,在分类上混乱和不科学,非常不便于珠饰研究方法的系统展开。
作者在第28页介绍了贝克(书中称培克)1928年提出的珠饰研究的五要素:形状、穿孔、颜色、材质和装饰。实际上,笔者及很多国外很多学者[21]在做珠饰研究时关注的要素要更为复杂。这些珠饰研究要素包括材质、颜色、大小、形状、制作工艺、外观纹饰等。其中制作工艺又包括制作成型工艺、颜色处理工艺、装饰实现工艺、钻孔工艺。每项工艺内容还要再细分,例如钻孔工艺涉及钻孔方法(如凿钻、预留孔、对钻、单向钻等)、钻头技术(如钻头材质、钻头形状、钻头长度、钻头与钻杆连接技术、组合钻头技术、钻头辅助研磨砂技术等)、钻具(如手钻、弓形钻等)、钻床和夹具、钻具技巧等等。系统科学的珠饰研究方法的第一步,是对珠饰进行系统科学的分类。
作者在书中列举的一些珠饰类别,表面上看似乎很清晰,实际上不便于对考古出土珠饰材料展开研究。例如作者珠饰分类中的钠钙玻璃珠类型,看似界定非常准确清楚,而且西周至汉晋时期的钠钙玻璃珠饰来自国外,已经有极其充分、科学的实验研究支撑。实际上,已进行成分分析的国内考古发掘玻璃珠饰是极少数的。按照目前国内的文物管理办法和文博系统的实验条件,很难开展对数以十万计,甚至几十万计的玻璃珠饰一一进行成分分析。因此很难将国内出土的钠钙玻璃珠作为一个大类,进行类似蜻蜓眼纹饰玻璃珠那样的系统研究。钠钙玻璃珠饰的确是直接的外来珠饰,有类似属性的还有与东南亚关系密切的钾玻璃珠、与印度关系密切的高铝玻璃珠等。所以,对费昂斯以外的玻璃珠饰研究时,通常按外观和工艺特征做为二级分类标准,如蜻蜓眼纹饰玻璃珠、马赛克玻璃珠、缠丝纹玻璃珠、双锥多棱玻璃珠等等。小彼得·弗朗西斯提出的印度-太平洋贸易珠,按工艺和外观特征,可以称为单色拉丝法玻璃粒珠。在二级分类的基础上,再讨论其中涉及不同化学成分的玻璃珠饰问题。例如按化学成分,蜻蜓眼纹玻璃珠可以再分为来自国外的钠钙蜻蜓眼纹玻璃珠和中国本土生产的铅钡蜻蜓眼纹玻璃珠。
作者书中讨论的13类珠饰中,有些分类不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作者书中第118页第二章第八节讨论的壶形珠。在贝克的著作《珠坠分类与命名》中亦没有定义一类“壶形珠”。[22]作者引用和参考贝克分类和命名方法的几个坠饰例子,如作者书中第119页-图2-40-6在贝克著作中被称为小玩意坠饰(Gadrooned Pendant,埃及22王朝费昂斯珠, 公元前945-前715年),作者书中第121页-图2-41-8在贝克著作中被称为花瓶珠(Vase Bead,古埃及12王朝,约公元前2000年),作者书中第121页-图2-41-9在贝克著作中被称为壶形珠(Jug bead,罗马时代)。[23]作者书中第121页-图2-41中引用杜宾著作《珠史》的两枚壶形珠为例。但在杜宾原作中并未将其壶状珠进行单独分类和论述,只在《珠史》第51页有38号和39号两张称为壶状珠(Jug bead)的插图,[24]插图备注中对两枚珠饰的年代、来源和现存地进行说明。可见国外主要珠饰学者也没有单独的“壶形珠”研究分类,可能考虑到其并非一类广泛出现,而且是没有普遍分类意义的珠饰。作者所列举的一些国外珠饰例子,也只是零星的出现于地中海局部等地区,而且年代跨度太大,形态和材质上也看不出直接的关联,并不能代表“西方”的普遍现象。作者自己也说 “并不肯定二者(中国壶形珠与国外壶形珠)之间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作者在第278-280页的附表九-中国出土西周至汉晋时期壶形珠一览表中,列举了来自23个墓葬或遗址出土的“壶形珠”。笔者大致查阅了作者引用的发掘资料,其中作者书中第119页列举的出土于三个四川战国中晚期墓葬的轴向穿孔的11枚铜制壶形珠饰(作者书中图2-40-1、图2-40-3、图2-40-4)、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出土的颈部穿孔的两枚玉材质壶形坠饰可归入作者所称“壶形珠”。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金瓶形珠饰勉强可以归入作者所称“壶形珠”。湖南湘乡东汉墓出土的铜“圆锤形”珠饰(作者书中图2-40-6)与贝克称小玩意坠饰近似[25],不适合归入作者所称“壶形珠”。四川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出土战国中晚期铜壶形器、云南昭通鸡窝院子汉墓出土东汉早期青铜双耳罐、甘肃酒泉下河清东汉墓出土红铜器均为无穿孔,显然不是可佩带的饰物,而是实用的小型铜器或作为冥器入葬的大型铜器的微缩版。云南呈贡天子庙滇文化墓出土的5件玛瑙珠饰为滇文化特有的鼓形珠,在江川李家山亦有出土[26],非作者所称“壶形珠”。湖南资兴东汉墓出土玻璃“扁壶形”珠饰,根据发掘报告和简图判为两端束领的糖果形玻璃珠[27],这类珠饰与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展出的合浦文昌塔153墓出土的糖果形玻璃珠类似,非作者所称“壶形珠”。湖南长沙黄泥塘两晋墓出土金饰与作者所称“壶形珠”亦不同。作者书中附表中余下绝大部分珠饰材料在引用来源中都无图可参考,只是发掘者描述为“花瓶”状、“壶形”、“扁壶形”、“垂球”状、“瓶状”、“壶”状,实际上这些简单描述并不能说明其就是如前述四川战国墓出土铜制壶形珠类似的饰物,实际情况可能有很大出入。例如作者列入“壶形珠”一览表的广西合浦九只岭M5和M6a的“壶形珠”,在发掘报告中描述为“水晶”“扁壶形”珠饰。但是发掘报告中却没有提供照片和线图。但是笔者在《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的图版中,找到了这两枚珠饰的彩图,分别为图版四-3和图版四-4(图4)[28]。实际上这两枚珠饰为玻璃材质,非报告中的“水晶”,而且是两枚“双胜”佩[29],并非作者所称“壶形珠”。作者附表九中至少还有6处汉晋时期墓葬的发掘报告描述有“扁壶形”珠饰或“扁壶饰”,有可能都属于合浦九只岭汉墓的情况。可见作者用于论述“壶形珠”的考古材料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与书中关注的“外来珠饰”和“外来文化”影响关系不大。甚至很多被引用的考古发掘材料,最后被发现归入是错误的。该类珠饰在作者书中语境下,不具有讨论的价值。

图4:广西合浦九只岭出土玻璃胜形佩(采自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
作者书中第76页第二章第四节开始论述蚀花珠的内容,题目为“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国内用“肉红石髓”指代英文中“Carnelian”这种矿物,较早可见于1974年夏鼐先生以作铭为笔名所著文章《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从夏鼐先生文章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夏鼐先生使用这种矿物命名依据为1954年科学出版社版的《矿物学名辞》。夏鼐先生还写道再早些时候,1933年商务版《地质矿物大辞典》和1932年商务版《百科名汇》,还称之为“鸡血石”[30]。可见不同时期,人们对同一种矿物的命名可能会不同。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先生,在考古学研究中涉及矿物名称时,使用的是地质学的矿物定名,这既是严谨治学的反映,也是统一学术语言的需要。统一的学术语言,可以避免在多学科交流中发生歧义和误解。在学科交叉如此频繁且深入的今天,统一学术言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2006年5月,地质出版社出版了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张蓓莉主编的《系统宝石学》一书,该书到2016年已经重印10次,是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指定教材,也是目前地质矿物与宝石相关学术言语的汇集。在2006年版的《系统宝石学》中,我们找不到“肉红石髓”的条目,因为现在地质学和矿物宝石学把这种矿物称为红玉髓[31]。可见至少在近十多年时间里,考古学界还在使用地质学界已经过时的矿物名称。这种情况在考古学界非常普遍。我们经常能看到考古发掘报告、考古和历史研究文章、甚至博物馆标签在文物的矿物名称和材质上出现错误和不规范,例如误把费昂斯珠写成绿松石珠,把玻璃珠甚至石珠称为料珠,把红玉髓称为红宝石等等。所以当下在考古研究中使用统一的地质学矿物名称,已显得非常迫切。
在此,笔者有必要引述一下《系统宝石学》[32]中,对玉髓、玛瑙、红玉髓、白玉髓的定义和相关材质的特征。玉髓、玛瑙、红玉髓、白玉髓都属于石英质玉石。石英质玉石的化学组成主要是二氧化硅,另外可能还存在少量铁、铝、钙、钛、锰、钒等微量元素。玉髓和玛瑙是隐晶质石英玉石的两个品种。玉髓是超显微隐晶质石英集合体。单体呈纤维状,杂乱或略定向排列,粒间微孔内充填有水分和气体。可含铁、铝、钙、钛、锰、镍、钒等微量元素或其他矿物的细小颗粒。根据颜色和所含其他矿物,玉髓可细分为 白玉髓、红玉髓、绿玉髓、蓝玉髓等。玛瑙是具有带状构造的隐晶质石英质玉石。按颜色、条带、杂质或包体特点,玛瑙可以细分为很多品种。如按颜色可分成白玛瑙、红玛瑙、绿玛瑙等。按条带可分成缟玛瑙;当缟玛瑙的条带变得十分细窄,又可称为缠丝玛瑙。红玉髓是颜色为红至褐红色的玉髓,由微量铁元素致色,微透明至半透明。白玉髓是颜色为灰白到灰色的玉髓,成分单一,呈微透明至半透明。实际上,宝玉石行业使用的纯红玉髓料块通常都是从红玛瑙矿石上切割下来的,即制作红玉髓和红玛瑙珠的材料来自同样的矿石。
具体到作者书中第76页,有关红玉髓材质的描述应参考地质学和矿物宝石学的相关定义和描述。例如作者书中称红玉髓“是一种晶质体玉石”也是不准确的。红玉髓是隐晶质石英集合体,隐晶质集合体与晶质体当然不同。
蚀花珠大致分两类,蚀花红玉髓珠和黑白蚀花珠,前一种是在红玉髓珠上进行蚀画图案,后一种是通过一定的工艺技术,在玉髓或玛瑙上呈现人为的黑白颜色纹饰。有关蚀花红玉髓和黑白蚀花珠的制作工艺,笔者将另有论述,不再赘述。黑白蚀花珠使用的矿物材质可以是白玉髓、红玉髓和玛瑙[33]。作者书中显然把所有的蚀花珠都称为蚀花红玉髓珠(作者书中称为“蚀花肉红蚀髓珠”),这是错误的。夏鼐先生在1974年的文章《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中,亦区分了“肉红石髓珠和蚀花的玛瑙珠”[34]。作者书中第71页-图2-21-广西贵县鱼种厂东汉墓出土的足球纹黑白蚀花珠[35]、第72页-图2-22的所有足球纹黑白蚀花珠、第87页-图2-30-1-新疆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墓地M5出土的蚀花珠、第87页-图2-30-10-斯坦因在和田采集的蚀花珠等,均为黑白蚀花珠,而作者书中均归为蚀花红玉髓珠,显然是错误的。新疆是国内蚀花红玉髓珠和黑白蚀花珠出土数量最多的地区,除了赵德云先生书中列举的蚀花红玉髓珠,笔者在相关文章还有更多补充[36]。黑白蚀花珠与蚀花红玉髓珠都是外来珠饰,在中国很多西周至汉晋时期的墓葬都有出土,例如西藏阿里地区曲踏墓地[36]、新疆塔什库尔干曲曼墓地[37]、1974年发掘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女巽]墓[38]等。
作者书中在论述蚀花红玉髓时,出现了一些引用错误或解读错误。作者书中第82页和第87页-图2-31-3中描述了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M8出土的白色眼圈纹板状玛瑙珠,作者书中认为“汤惠生判断位自然纹理,不确,从其照片观察,边缘周正,不可能是自然纹理,且圆内区域与圆外截然分开,色泽略浅,应是在腐蚀过程中造成的”。作者书中还专门把此珠编为“Cb型”“蚀花肉红石髓珠”,并在随后章节中进行论述。笔者查阅了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撰的《上孙家寨汉晋墓》[40]一书,同意汤惠生的观点。首先这枚珠饰是玛瑙材质,不是红玉髓。其次,上孙家寨乙M8出土的这枚白色眼圈纹板状玛瑙珠采用的是分层玛瑙材质制作,利用玛瑙层理中的白色条带,打磨出一圈白色眼圈纹的效果。这类白色眼圈纹玛瑙板状珠从公元前1900-前1700年印度河谷文明的后哈拉帕时期即出现[41];大英博物馆和纽约摩根博物馆都收藏有刻着整圈楔型文字的中巴比伦和新巴比伦时期的白色眼圈纹板状玛瑙珠;伊朗苏萨卫城一座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后期的公主墓中,出土一条穿有14枚大小接近的白色眼圈纹板状玛瑙珠项链[42];塔克希拉公元前3世纪的毕尔古堆遗址(Bhir Mound)亦有这类珠饰出土[43]。这种白色眼圈纹板状玛瑙珠是一种外来珠饰,而且在国外考古遗址中有广泛的出土记录,亦可以作为一种玛瑙珠饰类别进行讨论。显然作者书中未能囊括这些国外发掘材料,在这类玛瑙矿物的材质和工艺判断上出现了偏差,将其归入一个错误的讨论体系,造成作者书中与之有关的分类和论述也失去应有意义。
作者书中第87页-图2-31的另外两枚赵氏“C型蚀花肉红石髓珠”的考古材料辨别和归类亦有问题。图2-31-1的珠饰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滇文化墓地M24,笔者查阅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图版二三-2,发现这枚珠饰其实为多层条带眼纹缠丝玛瑙珠[44],这种多层条带是缠丝玛瑙的典型特征[45]。与青海大通孙家寨那枚白色眼圈纹板状玛瑙珠情况一样,作者书中进行了错误的分类和讨论。作者书中第87页-图2-31-2的珠饰,属于非常典型的贝克蚀花红玉髓分类分期图表的后期(late Period,公元600-1000年)C群,并非早期(Early Period,公元前2000年之前)A群[46]。大英博物馆的圣乔治·辛普森对这类蚀花红玉髓珠做过很好的研究。这类蚀花红玉髓珠在萨珊至伊斯兰早期的遗址中均有出土记录[47]。作者书中所谓“C型蚀花肉红石髓珠”(包括两个亚型Ca和Cb)所依据的三个考古资料判断都是错的,因此,作者书中的这个珠饰分类及随后的相关讨论已失去意义。
作者书中对矿物和珠饰材质的误判,还体现在书中第70-72页,有关广西贵县鱼种厂一号汉墓出土的足球纹黑白蚀花珠材质的分析判断上(图5)。熊昭明和李青会在《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一书中,对出土于广西贵县鱼种厂一号汉墓的两枚足球纹黑白蚀花珠分别进行P-XRF(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和P-XRD(X射线衍射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可以确定珠饰的材质为玛瑙或玉髓[48]。两位研究者的分析方法严谨,实验结果讨论清晰,结论可信。但是赵德云先生在书中第70页说“令人有疑惑的是,测试者采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和X射线衍射分析,对同一件标本主要成分进行测试,前者结果为硅,后者为低温石英”。显然作者不了解X射线荧光光谱和X射线衍射两种分析方法的原理和应用,也不了解如何判读实验分析数据。XRF(X-Ray Fluorescence)即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因其实现原理特点,XRF适合用于各种宝石的无损测试,分析实验样品的元素种类和含量[49]。因此在XRF的谱图上呈现的是各种元素的峰值。在《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中,广西贵县鱼种厂一号汉墓出土的足球纹黑白蚀花珠XRF分析图谱上呈现的是硅(Si)元素的高峰值[50]。XRD(X-ray diffraction)即X射线衍射分析,因其工作原理特点,XRD适合用于实验矿物样品的物相和结构[51]。因此在《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中,广西贵县鱼种厂一号汉墓出土的足球纹黑白蚀花珠的XRD分析,检测出主要组成物的物相为低温水晶(α-quartz)[52]。低温水晶(α-quartz)包括自然显晶(水晶等)或隐晶石英(玛瑙或玉髓等)[53],当然不可能是非晶态的人造玻璃。作者书中对X射线荧光光谱和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的质疑,其实反映了作者对科技分析方法的不了解。

图5:广西贵港(原贵县)渔种场出土足球纹黑白蚀花珠(采自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
在书中,作者表示通过珠饰彩图判断,认为是玻璃的可能性更大些。作者没有给出判断依据。但是再次说明作者对矿物和珠饰材质的不了解。其实通过贵县鱼种厂汉墓出土足球纹黑白蚀花珠的一些表面特征,也能基本判断其为玉髓或玛瑙,并非玻璃材质。首先,《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中描述贵县鱼种厂汉墓出土足球纹黑白蚀花珠“穿孔为喇叭形、穿孔口有破碎痕迹,判断为人工钻孔”[54]。作者在书中第30页珠饰穿孔部分,也写道“玻璃珠…穿孔也就自然形成了”,即大部分的玻璃珠饰都是预留孔,而“石珠…一般采用对穿法…中间会留下结合部”。贵县鱼种厂汉墓出土足球纹黑白蚀花珠为人工钻孔,而且通过彩图可见对钻错位造成中间较小的结合部[55]。
如果这还不够,还可以结合材质的特点。《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中记录贵县鱼种厂汉墓出土足球纹黑白蚀花珠“穿孔口有破碎痕迹”。我们知道大多数玻璃的破碎后具有贝壳状断口,并在断口表面显示出玻璃光泽,只有含有铜晶体包体的金星石玻璃才会形成锯齿状断口[56](金星玻璃要到清代才创烧成功)。通过观察贵县鱼种厂汉墓出土足球纹黑白蚀花珠照片[57]中,孔口破损断口为锯齿形,并不见玻璃材质断口的贝壳状,亦不见玻璃光泽。综合以上科学仪器分析和外观观察,都可判断贵县鱼种厂汉墓出土足球纹黑白蚀花珠的材质为玛瑙或玉髓,非玻璃也。当然还有塔克希拉[58]和阿富汗黄金之丘等出土文物[59]作为佐证。
作者书中存在与矿物和珠饰材质基础知识有关的问题,还包括琥珀和青金石。第101页第二章第六节作者写道“琥珀并不是矿物,亦非一般意义上的化石,而是一种完全的有机质”。对琥珀正确的认识应该是,琥珀是珍贵的有机宝石,是经过地质作用形成的化石[60]。在矿物学分类中,琥珀属于有机准矿物[61]。从作者书中第101页的表述可见的逻辑概念为:琥珀“是一种完全的有机质”,所以“琥珀并不是矿物”。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矿物学分类中,包括有机矿物及准矿物大类[62]。另外,笔者于2016年地质学核心学术期刊《岩石矿物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中国古代琥珀珠饰鉴定及其产地初探》,介绍通过科学仪器分析琥珀成分及内含物,进行矿物鉴定和确定古代琥珀珠饰矿物来源的研究方法(图6)。笔者运用红外吸收光谱分析方法,观察到西汉至魏晋南北朝的琥珀珠饰样品在红外光谱的1260 cm-1到1120 cm-1之间有低于1370 cm-1和1010 cm-1的缓坡肩峰,初步确定西汉至魏晋南北朝琥珀珠饰的矿物原料来自波罗的海,笔者还初步梳理了这时期中外琥珀贸易的路径[63]。

图6:中国汉晋时期琥珀印胚(采自覃春雷《中国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琥珀来源初探》)
作者书中第135页写道“青金石或译为‘天青石’”,这虽然是作者引述,但是这也反映了很多学者对青金石矿物的认识,所以有必要在此一并说明。在矿物宝石学中,青金石与天青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矿物,青金石属于硫酸铝硅酸盐矿物,对应矿物的英文名称为Lapis Lazuli,化学成分为(NaCa)8(AlSiO4)6(SO4,Cl,S)2;天青石属于硫酸盐矿物,对应矿物的英文名称为Celestite,化学成分为(Sr,Ba)SO4;天蓝石为磷酸盐矿物,对应矿物的英文名称为Lazulite,化学成分为MgAl2(PO4)2(OH)2[64]。所以建议相关学者在文献翻译、引用和研究论述中,不要把青金石、天青石与天蓝石名称混淆使用,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不同的地质学矿物。
作者书中对一些玻璃珠饰工艺的认识上也存在问题。第58页作者引述艾森1916年“推想”的所谓“截棒技术”:“将玻璃棒放在不同颜色的玻璃液中依次蘸泡,当其凝固之后,截成小薄片,每一薄片九成为一个制作好的眼珠,只需将其嵌入未凝固的母体即可”。这毕竟是100年前的“推想”!古代珠饰工艺的研究不仅需要推想,还需要先进的技术分析手段和工艺复原实践。实际上,多层多色玻璃棒(Overlay Canes)技术,需要在依然软热的中心玻璃棒周围,一条条的轴向沾上同样软热的单色玻璃条,然后通过滚压或借助一定的工具使新沾上尚热的单色玻璃条包裹中心玻璃棒,并回炉加热烧结;然后再返回前一个步骤继续沾上新颜色软热玻璃条;如此就可以得到多层多色玻璃棒[65]。了解和参观过多色玻璃制作过程的人都知道,玻璃是不可能像水一样蘸泡的。有关蜻蜓眼纹饰玻璃珠的制作工艺,笔者更倾向于认可日本玻璃艺术家的工艺复原尝试。大部分蜻蜓眼纹饰玻璃珠的“眼睛”部分,是乘着玻璃珠的主珠玻璃材料还软热的时候,用烧化或软化的玻璃一层沾压上去,再滚压成形的[66]。有些不经滚压而层层沾滴上去的热玻璃汁液,修形冷却后就成了椎凸蜻蜓眼纹玻璃珠[67]。战国至汉代中国本土制作的蜻蜓眼纹饰玻璃珠,可能是先将主珠和“眼睛”部分分别制作,然后将“眼睛”与主珠沾连再回炉烧结,经滚压而成。“眼睛”部分也需要一层层的粘而成[68]。很多中国战国蜻蜓眼纹玻璃珠,在发掘时被发现眼部贴片已脱落或容易脱落,可能就是因为以上描述工艺造成。李青会等在研究古代蜻蜓眼纹玻璃珠时,引入OCT(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即光学相干层析成像技术分析方法,可以观测“眼睛”部分的结构特征。笔者根据李青会公布的OCT分析蜻蜓眼纹玻璃珠图像,发现赵德云先生书中图2-9和图2-11中大部分类型的蜻蜓眼纹玻璃珠均多层结构[69]。OCT的研究方法也印证了日本玻璃艺术家所做的古代蜻蜓眼纹玻璃珠工艺复原是正确的。而艾森100年前推想的所谓“截棒技术”在这些古代玻璃珠饰眼睛中未被观测到。截片同心圆蜻蜓眼玻璃珠的技术应用可能相对较晚。日本玻璃艺术家也曾对这技术进行工艺复原尝试[70]。另外,通过OCT分析方法对蜻蜓眼纹玻璃珠的研究,也证明作者书中第61页“赵氏C型嵌环眼珠”分类和工艺想象是错误的。作者在书中论述“嵌环眼珠(Impressed Ring Eye Bead),将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料制成细条,嵌入母体,大致呈环状,成为‘眼眶’,环内的母体颜色形成眼珠的效果”。作者书中并未给出工艺推测的依据。但是,通过OCT仪器分析和日本玻璃艺术家的对古代蜻蜓眼纹玻璃珠的工艺复原实践[71],证明作者书中的工艺想象与实际情况不符。所以无论是作者书中引用艾森的所谓“截棒技术”,还是作者推想的“嵌环”式蜻蜓眼纹玻璃珠制作工艺都是错误的工艺技术推想,造成作者书中引用其所作的讨论都存在技术性缺陷。
作者书中第160页认为中国工匠在制作蜻蜓眼玻璃珠时,受到了蚀花红玉髓珠图案的影响,理由是蚀花红玉髓珠与蜻蜓眼纹玻璃珠一样,也采用眼睛图案进行装饰。这种联想可以理解,但是其逻辑和依据实在占不住脚。首先,根据考古材料,中国开始制作蜻蜓眼玻璃珠的时间可能始于战国早中期,参考贝克的蚀花红玉髓珠的分期和分类可知,蚀花红玉髓珠上的眼圈纹图案多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的早期(A期)[72]。第二期(公元前300年-公元200年)的蚀花红玉髓珠图案中眼圈纹图案比较少[73]。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有一千多年的空白期,这期间缺少第一期蚀花红玉髓珠的出土资料,即第一期蚀花红玉髓珠消失一千多年后,这种红玉髓蚀花技术才又重新出现。而且无论是哪儿一期蚀花红玉髓珠,主要集中出现于新疆和云南,在中原地区极少出现,足见其并未在中原地区流行,更谈不上形成对中原地区广泛出现的蜻蜓眼纹玻璃珠的纹饰影响。无论是时间和空间上,蚀花红玉髓珠与中国自制的蜻蜓眼纹玻璃珠都少有交集。考古证据上亦不能支持。作者书中举曲阜鲁国故城战国中期或稍晚M58出土的珠饰为例,可知到目前为止华北、华东、东北地区未见有蚀花红玉髓珠的出土记录。作者书中又举新疆洛浦山普拉汉晋墓出土的缠丝纹玻璃珠(作者原文“流云、斜线纹玻璃珠”)[74]与赵氏“B型蚀花肉红石髓珠”图案相近,作为玻璃珠图案模仿蚀花红玉髓珠的佐证。实际上,缠丝纹玻璃珠图案直接模仿自缠丝玛瑙,对此杜宾在《珠史》中有很好的研究和对比说明[75]。作者书中至少应该先试图证明山普拉汉晋墓出土的缠丝纹玻璃珠是中国本地生产珠饰,才适合做为论证依据。相反,山普拉汉晋墓出土的缠丝纹玻璃珠更有可能是外来珠饰。所以,作者书中所述蚀花红玉髓珠与蜻蜓眼纹玻璃珠之间存在互相影响,没有充分的考古资料支持。从逻辑上,中国出土的蚀花红玉髓珠与中国本土制作的蜻蜓眼纹饰玻璃珠,在时间和空间上,极少有交集,当然不能形成纹饰上互相影响的依据。
在书中第136页,作者列举所谓人头坠子作为外来珠饰的例子。其中引用的四枚所谓“人头坠子”珠饰,为1997年购自青岛小古董店,并非考古出土材料,存在非常大的疑问(图7)。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家瑶老师请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保护实验室,对这四枚市购品进行成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其成分为铅钡玻璃,安家瑶老师认为“铅钡玻璃在东汉之后就不再出现”,以此“排除了是现代人制作的赝品的可能性”,并认为中国战国-西汉的工匠用铅钡玻璃仿制了少量人头坠子[76]。

图7:购自青岛古董店的玻璃“人头坠子”(疑似现代仿品)(采自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
赵德云先生表示同意安家瑶老师的意见。笔者查阅了安家瑶老师在《玻璃考古三则》中公布的人头坠子的三组成分分析数据,并与《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中公布的700余件考古出土的中国古代玻璃器成分分析数据进行比对[77],发现《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列举的铅钡玻璃成分中铅含量至少是钡的两倍以上,而《玻璃考古三则》中样品2的钡含量是铅的两倍多,这显然不合理。另外,根据明末清初人孙廷铨所著《颜山杂记校注》中的山东博山地区存在玻璃制作的记录,“琉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礁以锻之,铜铁丹铅以变之”,又曰“法如白,加铅焉,多多益善,得牙白”,可知直到明末清初,山东博山地区依然使用古法制作铅钡玻璃[78]。《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中也记录了隋唐至明代期间,可能与铅钡玻璃制作有关的古代文献[79]。所以安家瑶老师通过确定成分为铅钡玻璃来认为其非现代赝品的意见值得商榷。实验数据中存在的铅钡比的问题,也说明这几件购自青岛小古董店的人头坠子极有可能为现代臆造品。无独有偶,2001年,罗伯特老师在《珠饰》杂志(《Ornament》)上发表文章《从器物研究仿制工艺品的动力之源》,其中也公布了与安家瑶老师文章中近似的腓尼基人头坠的现代仿品(图8)[80]。因为研究对象的问题,造成作者书中所做与人头坠子有关的论述的可靠性亦存在问题。由于引用不可靠的研究材料作为珠饰分类和研究依据,对其他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研究者也容易产生误导。

图8:仿腓尼基玻璃人头坠(现代)(采自Robert Liu《Deducing Attitudes from Artifacts》)
作者书中第151页,引述关善明有关春秋以后铅钡为国产费昂斯助熔剂的论点[81]也值得商榷。根据董俊卿等对考古发掘的西周至春秋多墓葬出土的费昂斯珠饰分析研究,中国西周至春秋费昂斯的成分除二氧化硅外,依然以钠钾铝铜为主[82]。对考古发掘的费昂斯珠饰成分研究说明,春秋时期的费昂斯珠助剂依然是含钾钠的草木灰,并非铅钡。关氏的论述是基于对其个人收藏的费昂斯珠饰分析。由于关氏个人收藏的费昂斯珠饰缺乏出土地地层和来源信息,其说服力自然不如基于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可靠。所以引关氏结论作为作者书中观点“铅钡”“费昂斯”“为春秋末、战国早期中国铅钡玻璃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的支撑,因论据的可靠性存在问题,造成作者书中所述论点的不可靠。
作者书中因为引用不可靠资料而产生错误或误导性结论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书中第90页,作者引用《藏珠之乐I》认为“‘板状眼珠’,可能渊源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人的护身符‘乌贾’(Udjat),指太阳神霍拉斯(Horus)的眼睛,其后在埃及十分流行”。其中有非常明显的错误。只要对古埃及文明有初步了解的人都知道,荷鲁斯神(Horus)(作者引译为霍拉斯)是古埃及的鹰神,并非太阳神[83],亦非两河文明的苏美尔人的神。而乌贾(Udjat),也被称为荷鲁斯之眼,是古埃及最重要的护身符之一[84]。这只能说明研究者对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缺乏基本的认识,才导致引用张冠李戴的不可靠资料。有关眼纹饰板状玛瑙珠的源流,笔者在前边评介赵德云先生用青海大通孙家寨珠饰材料问题时,已经引述克诺耶尔教授的研究进行说明[85],不再赘述。
作者书中第146页引述《珠史》写道“在埃及语中,‘sha’意味‘好运气’,而‘sha-sha’意为珠子,表明珠饰在埃及的护符意涵”。实际上,这是《珠史》中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音符[sha](表示读音的象形文字字符)的误判。每个古埃及象形文字由表读音的音符和表含义属性的意符组成[86],就像中国小学生作业中写汉字要在上边标上拼音一样。参考埃及学家罗西尼(Stéphane Rossini)所著《如何读写古埃及象形文字》(Egyptian Hieroglyphics: How to read and write them),画写成荷花池的音符[sha]是134个古埃及象形文字音符之一,但是180个古埃及象形文字意符中没有[sha],说明[sha]只是音符[87],并不表意。象形图案音符[sha]用于拼写所有含sha读音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但不影响该象形文字的含义。古埃及语中,项链和珠子读作“sha-shat”,所以需要用音符[sha]来拼写古埃及象形文字项链和珠子的读音的一部分,意符(限定符)是一个画写作项链的符号[88]。如古埃及语中动词旅行也读作“sha”,所以也需要用音符[sha]来拼写古埃及象形文字动词“旅行”的读音部分,表示文字含义属性的是后边画写为人脚行走的字符[89]。因此,《珠史》的作者明显也不了解古埃及语言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音符与意符的关系及作用,过度解释了珠子在古埃及文化的含义,并不能以此作为作者书中观点“珠饰在埃及的护符意涵”的依据。作者书中以此作为其论点“西方珠饰与宗教信仰结合紧密”的依据是不适当的。
书中第146页,作者举叙利亚东部布拉克丘(Tell Brak)的“眼睛神庙”的台基出土大量珠饰,作为其论点“西方珠饰与宗教信仰结合紧密”的另外一个依据,也同样存在问题。首先,在两河文明的神系中,并不见这么一位“眼睛神”,而且在叙利亚布拉克古堆遗址(Tell Brak)以外,未见其他类似的神庙[90]。所谓的“眼神庙”可能属于某位“母亲神”崇拜的庙宇[91],所以命名为“眼神庙”本身是早期发掘者的误称。其次,将各种奇珍异宝置于建筑和庙宇的塔基,在古印度和中国也同样广泛存在,并不能表明被埋藏于斯的器物本身即与宗教信仰结合紧密,奇珍异宝在世俗生活中同样是财富与身份的体现,这在世界各地都广泛适用。而且两河文明几个重要的墓葬发掘,如乌尔城遗址的乌尔王陵[92]和尼姆鲁德的新亚述时期王后墓葬[93]都出土了数量极大的玛瑙珠、红玉髓珠、青金石珠、黄金珠饰等。我国西周时期的韩城梁代村、侯马晋侯墓地、宝鸡[弓鱼]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大量红玉髓珠、费昂斯珠和玉珠饰等,其亦是作为墓主人身份、地位和财富写照。珠饰在彰显佩戴者身份、地位和财富方面,两河流域文明与古代中国显然是非常相似的。
书中第146页,作者还引述资料写道“在印度,最早可确认的护符年代在公元前1700年…一个重要特征是与宗教联系紧密…”。实际上,至少公元前2600-前1900年的印度河谷文明时期,已有护身符,在印度河谷遗址出土一种圆锥形的护身符,多出自女性墓葬[94]。珠饰,尤其是红玉髓和蚀花红玉髓珠饰是印度河谷文明非常重要的贸易商品,这些印度河谷文明的珠饰大量出现于两河流域和伊朗地区[95]。公元前1千纪的两河流域和伊朗地区,同样发现大量古印度的玛瑙、红玉髓珠饰[96]。佛教、印度教等宗教在古印度兴起而出现的计数念珠,的确与宗教联系紧密,但是其并不是古代印度珠饰及其历史的全部代表。至于作者书中还用“Cb型板状眼珠”和所谓壶形珠的作为佐证,笔者在前文已经详述过其书中论述的这两类珠饰的问题,不再赘述。
书中第124-125页,作者引述各种狮兽形珠饰(作者称“辟邪形珠”)资料,最后认为“狮形珠饰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后来传播至印度”。书中第147页,作者认为“辟邪形珠…显然应是作为护符传入印度后,可能与佛教的传播相结合”。书中第228页,“辟邪形珠可能源自地中海沿岸将珠饰制作成狮子形状的意匠,随着亚历山大东征,传播到印度”。从古代近东文明的考古资料看,乌鲁克后期至杰姆鲁德纳什尔时期(约公元前3300-前2900年)的遗址出土了各种材质的羊、牛、狮子等动物圆雕饰物[97]。伊朗苏萨卫城古堆遗址出土了公元前1500-前1200年的缠丝玛瑙狮子圆雕饰物[98]。泰国班东塔贝遗址出土了一枚红玉髓狮子型珠饰,研究者认为其可能来自印度的影响[99]。班东塔贝遗址的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100],说明印度出现狮子型珠饰要早于亚历山大东征,可能来自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对东方的影响。所以作者书中有关狮兽形珠饰的来源、历史、传播等内容亦存在问题。
综合以上作者书中认为珠饰在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等文明地区“与宗教信仰结合紧密”的依据均不充分、甚至是过度解读或错误的,所以作者书中希望构建的国外珠饰与中国珠饰使用传统差异的理论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甚至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作者书中基于此理论基础进行的论述,自然不具备说服力。
书中第139页第三章第一节“中外珠饰制造材料和使用传统的差异”,作者写道“新石器时代以后,西方世界对于珠饰材料的选择,比较偏重黑耀石、琥珀和青金石等贵重材料”。“其中青金石可谓是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材料”。第140页,作者写道“我们认为,西方珠饰偏好选择那些材质罕见、质地坚固、色泽肃穆的原材料来制作,这大概和珠饰在西方文化中护符意涵较强有关”。“西方珠饰制造中原材料的选择,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金银一类贵金属的重视”。从考古资料看,几乎很少见到黑耀石珠饰出现于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伊朗和古印度等地区和文明的遗址中。黑耀石一般被用制作工具[101]。琥珀除了出现于波罗的海周边地区、意大利的伊特鲁尼亚文明和罗马文明地区,在两河流域、伊朗、埃及、中亚和古印度都不见流行。所以作者说“西方世界对于珠饰材料的选择,比较偏重黑耀石、琥珀”,的确不知所云。青金石珠饰在公元前3千纪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遗址,确有大量出土记录。在整个公元前2千纪,青金石在两河流域的使用较之前大为减少[102]。公元前900-前600年的新亚述时期,青金石珠饰较之前有所增加[103]。但是,公元前3千纪后,青金石再没有达到苏美尔文明时期的受重视程度[104]。古埃及人非常重视青金石,但是青金石珠饰在古埃及珠饰中的比例是比较小的,远不如红玉髓珠、费昂斯珠、紫水晶(中王朝至新王朝)、黄金珠饰等等。伊朗的情况和两河流域比较近似。青金石材质的珠饰在古印度一直都非常少[105]。相比之下,红玉髓或玛瑙在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伊朗和古印度等地区,包括东南亚,都是最受重视的珠饰。代表性的例子包括埃及阿尔拉洪遗址(El-Lahun)古埃及第12王朝墓葬[106]、乌尔城遗址的乌尔王陵(图9)[107]、尼姆鲁德的新亚述时期王后墓葬[108]、印度河谷文明柴胡达罗(Chanhu-Daro)玛瑙珠饰作坊[109]出土的珠饰。所以,从中国以西的几个重要古代文明的考古发掘资料看,红玉髓、玛瑙珠饰在国外珠饰的比重要远高于青金石和黄金。中国西周至汉晋时期珠饰,除了费昂斯和玻璃,最大宗的就是红玉髓、玛瑙等,还有部分水晶等,与作者书中所述西方珠饰与中国珠饰差别的情况相差甚远。所以,作者书中基于相对片面、不充分、甚至不准确的材料,引出的西方珠饰与中国珠饰差别的对比,以及书中随后基于此进行的讨论和结论,说服力都很弱,甚至是不正确的。

图9:伊拉克纳西里耶乌尔王陵出土黄金珠、红玉髓珠、青金石珠项饰(笔者摄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作者书中还有几处西方考古年代表述的明显错误上。书中第17页,“在乌尔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后的遗址中…”、第112页“‘焊珠工艺’(Granulation),最早的发现是在西亚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公元前四千纪)皇室墓葬”、第135页“早在公元前3500年的晚期欧贝德(Ubaid)文化时期”等。据乌利爵士1955年代发表的乌尔发掘报告,乌尔遗址最早的文化层是欧贝德时期,即公元前5900-前4300年[110],非作者书中称“公元前7000年”。根据考古证据显示,苏美尔王表记录的乌尔第一王朝对应的两河文明考古学年代为早王朝第三期,即处于公元前3千纪[111],并非作者书中称“公元前四千纪”。两河流域欧贝德文化时期为公元前5900-前4300年,而公元前3500年已经进入乌鲁克后期了[112],作者书中所说“公元前3500年”并非“晚期欧贝德(Ubaid)文化时期”。
作者书中对国外一些重要珠饰研究材料的掌握不够,引用的很多研究材料比较老化,也导致作者书中一些内容上的缺陷。例如美国华盛顿珠子博物馆曾出版一本重要的珠饰研究书籍《珠子的编年》(《A Bead Timeline》)[113],按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200年的顺序,介绍当时华盛顿珠子博物馆按年代陈列的珠子的考古记录、制作工艺等。其中就有作者书中第133页论述的“人面纹珠”。这种人面纹珠在泰国中南半岛的甲米地区有出土记录,年代约公元4世纪,而且华盛顿珠子博物馆亦收藏展出一枚这种马赛克人面玻璃珠(图10)。所以作者书中对营盘墓地出土的这枚玻璃珠饰的一些论述存在非常大的缺陷。由于篇幅的原因,笔者难以对作者书中存在的问题一一进行评介和资料佐证。希望作者能重新修订其研究框架,使其发挥出应有的学术价值。

图10:新疆尉犁营盘墓地出土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9)与泰国出土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的对比图(采自覃春雷《新疆尉犁营盘墓地出土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来源考略》)
从书中的珠饰材料和观点论述上看,作者已经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书中出现的缺漏和系统性的研究问题,更能说明珠饰考古研究的难度之大。可见珠饰并不是考古发掘的“小”材料。希望更多的考古工作者关注发掘中的珠饰材料,欢迎更多学者加入到珠饰考古的研究领域中,让这类考古材料充分发挥其作用,为考古工作者“透物见人”、还原历史增添一把利器。
注释
[1] Horace C. Beck, Etched Carnelian Beads Antiquaries Journal, 1933, 13 (4);Horace C. Beck, The Beads from Taxila,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o.65,Archacological Survey of India,1999;Horace C. Beck, 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 of Beads and Pendants, Bead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Bead Researchers, 2006, 18.
[2] Ian C. Glover, Helen Hughes Brock and Julian Henderson, Ornaments from the Past: Bead studies after Beck, The Bead Study Trust, 2003; Ian C. Glover and Berenice Bellina, Alkaline Etched Beads in Southeast Asia Ornaments from the Past: Bead studies after Beck, The Bead Study Trust, 2003: 92-107.
[3] Moore E., Myint. Aung, Beads of Myanmar,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1993, 81 (1).
[4] St John Simpson, Sasanian Beads: the Evidence of Art, Texts and Archaeology, Ornaments from the Past: Bead studies after Beck, The Bead Study Trust,2003.
[5] P.R.S Moorey. Ancient Mesopotam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9.
[6] Barbie Campbell Cole, Ancient Hard Stone Beads and Seals of Myanmar Ornaments from the Past: Bead studies after Beck, The Bead Study Trust, 2003.
[7] lan C. Glover and Berenice Bellina, Alkaline Etched Beads in Southeast Asia, Ornaments from the Past: Bead studies after Beck, The Bead Study Trust, 2003: 92-107,
[8] Jonathan Mark Kenoyer,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Jonathan M. Kenoyer, Stone beads and pendant making techniques A Bead Timeline: Prehistory to 1200CE,The Bead Society of Greater Washington,2003.Jonathan M. Kenoyer, Eye Beads from the Indus Tradition: Technology, Style and Chronology, Journal of Asia Civilizations, 2013, 36 (2).
[9] Robert K.Liu, Collectable Beads, Ornament, Inc., 1995.
[10] Peter Francis, Jr., Asia's Maritime Bead Trade: 300 B.C.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11] Lois Sherr Dubin, The History of Beads: from 100,000 B.C. to the present, Abrms, 2009.
[12] James W. Lankton, A Bead Timeline, The Bead Society of Great Washington, 2003.
[13] 同[11][12].
[14] Nia Xia, Ancient Egyptian Beads,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d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4.
[15] 作铭《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考古》1974年第6期。
[16] 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干福熹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覃春雷、孙傲《中国古代琥珀珠饰鉴定及其产地初探》,《岩石矿物学杂志》2016年第35卷增刊1;H.X.Zhao and Q.H. Li, Combined spectroscopic analysis of stratified glass eye beads from China date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Journal of Raman Spectroscopy,2017;覃春雷《从珠子角度看新疆“拜火教”遗址考古的疑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网站(中国考古网),2017年8月11日;覃春雷《丝路遗珠:记新疆发现的蚀花红玉髓珠》,《丝绸之路》2018年总第368期。
[17] 李胜荣、许虹、申俊峰等《结晶学与矿物学》,地质出版社,2013年,第188页;张蓓莉《系统宝石学>地质出版社,2016年,第375~377页。
[18] Nia Xia, Ancient Egyptian Beads,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and Springer -Verlag Berlin Heidelberg,2014;Jonathan Mark Kenoyer,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8, 139; Horace C. Beck, The Beads from Taxila,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No.65:43,Plate L.
[1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干骨崖》,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89、322、332页,彩版二~彩版二二;玉门市文化体育局、玉门市博物馆、玉门市文物管理所《玉门文物》,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7、168页,彩版一九。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红玛瑙珠(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藏,首都博物馆妇好墓发掘文物展)、广汉三星堆出土红玛瑙珠(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均为考古发掘的商代出土文物,年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
[20] 河南省博物馆藏西周时期虢国、应国墓地出土珠饰,山西省博物馆藏西周晋侯墓地出土珠饰,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韩城梁带村出土西周芮国红玛瑙、玉组佩。
[21] Jonathan M. Kenoyer, Stone beads and pendant making techniques A Bead Timeline: Prehistory to 1200CE, The Bead Society of Greater Washington,2003.
[22] Horace C. Beck, 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 of Beads and Pendants, Beads: Journal o f the Society of Bead Researchers, 2006: 18.
[23] 同[22]pp.25,pp33.
[24] Lois Sherr Dubin, The History of Beads: from 100, 000 B.C. to : he present, Abrms, 2009: 51.
[25] 同注[23]
[2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彩版一七一。
[27]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图版四。
[28] 同[27]
[29] 王薪《从汉墓考察西王母“戴胜”图像涵义及流变》,《西部学刊》2018年第6期(总第75期);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1988年第2期,第34页。
[30] 作铭《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考古》1974年第6期。
[31] 张蓓莉《系统宝石学》,第375~377页。
[32] 同上。
[33] lan C. Glover and Berenice Bellina, Alkaline Etched Beads in Southeast Asia, Ornaments from the Past: Bead studies after Beck, The Bead Study Trust, 2003: 92-107.
[34] 作铭《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第383页。
[35]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第171、172页,图版一七。
[36] 覃春雷《丝路遗珠:记新疆发现的蚀花红玉髓珠》,《丝绸之路》2018年7月总第368期;覃春雷《从珠子角度看新疆“拜火教”遗址考古的疑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官方网站-中国考古网,2017年8月11日。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阿里地区文物局等《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考古》2015年第7期。
[38] 巫新华《2013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的考古发掘>,<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
[39] 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娱墓》,《文物》1979年第3期。
[40]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第161页,图版八七。
[41] Jonathan Mark Kenoyer,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6.
[42] The British Museum Forgotten Empire: 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5: 177.
[43] Horace C. Beck, The Beads from Taxila,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o.65,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99:43,Plate I.
[44]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图版二三。
[45] 张蓓莉《系统宝石学》,第375~377页。
[46] 作铭《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第382页;H.C. Beck, Etched Carnelian Beads pl. LXX, pl.LXXI, Antiquaries Journal, 1933, 13 (4).
[47] St John Simpson, Sasanian Beads: the Evidence of Art, Texts and Archaeology, Ornaments from the Past: Bead studies after Beck, The Bead Study Trust, 2003: 65,66.
[48]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第171、172页、图版一七。
[49] 张蓓莉《系统宝石学》,第113~116页。
[50] 同[48]
[51] 李胜荣、许虹、申俊峰、李国武等《结晶学与矿物学》,第323页。
[52] 同[48]
[53] 同[51]
[54] 同[48]
[55] 同[48]
[56] 张蓓莉《系统宝石学》,第604页。
[57] 同[48]
[58] Horace C. Beck, The Beads from Taxila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lndia, 65: 45. Plate II.
[59] Victor Sariadin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From the Tillya-Tepe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Aurora Art Publishers, 1985: 233.
[60] 覃春雷、孙傲《中国古代琥珀珠饰鉴定及其产地初探》。
[61] 李胜荣、许虹、申俊峰、李国武等《结晶学与矿物学》,第291~295页。
[62] 同[61]
[63] 覃春雷,孙傲《中国古代琥珀珠饰鉴定及其产地初探》。
[64] 张蓓莉《系统宝石学》,第399、520、510页。
[65] E. Marianne Sterm, Birgit Schlick-Nolte, Early Glass of the Ancient World, Verlag Gerd Hatje, 1994:55-57;(日)由水常雄《玻璃》(原书为日文),平凡社,2008年,第28页。
[66] Takashi Taniichi, Yoshiro Kudo, Glass Beads in the World, Ribun Shuppan Co.,LTD, 1997: 118.
[67] Takashi Taniichi,Yoshiro Kudo, Glass Beads in the World, Ribun Shuppan Co.,LTD, 1997: 117.
[68](日)由水常雄《玻璃》(原书为日文),第55页。
[69] H.X. Zhao, Q.H. Li, Combined spectroscopic analysis of stratified glass eye beads from China date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Journal of Raman Spectroscopy, 2017.
[70] Takashi Taniichi, Yoshiro Kudo, Glass Beads in the World, Ribun Shuppan Co.,LTD, 1997: 119.
[71] H.X. Zhao and Q. H. Li, Combined spectroscopic analysis of stratified glass eye beads from China date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Journal of Raman Spectroscopy,2017;Takashi Taniichi, Yoshiro Kudo, Glass Beads in the World, Ribun Shuppan Co.,LTD, 1997: 118.
[72] H.C. Beck, Etched Carnelian Beads, pl.LXX, pl.LXXI, Antiquaries Journal, 1933, 13 (4).
[73] 同[72]
[74] 干福熹《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3页。
[75] Lois Sherr Dubin, The History of Beads: from 100,000 B.C. to the present, pp.53.
[76] 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文物》,2000年第1期,第89~91页。
[77] 干福熹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310~374页。
[78] 孙廷铨著,李新庆校注《颜山杂记校注》,齐鲁书社,2012年,第114、115页。
[79] 干福熹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第113~116页。
[80] Robert K.Liu, Deducing Attitudes from Artifacts, Ornament, 2001,24 (4).
[81] 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第14、15、106~113页。
[82] 干福熹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2016年,第54-63页。
[83] Ian Shaw, Paul Nicholson, The Illustrated Dictionary of Ancient Egyp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8: 150, 151.
[84] Ian Shaw, Paul Nicholson, The Illustrated Dictionary of Ancient Egyp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8: 338.
[85] Jonathan M. Kenoyer, “Eye Beads from the Indus Tradition: Technology, Style and Chronology, Journal of Asia Civilizations, 2013, 36(2).
[86] Stéphane Rossini, Egyptian Hieroglyphics: How to read and write them,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9:7-8.
[87] Stéphane Rossini, Egyptian Hieroglyphics: How to read and write them, pp.81-91.
[88] Stéphane Rossini,Egyptian Hieroglyphics: How to read and write them, pp. 58.
[89] 同[88]
[90] Jeremy Black, Anthony Green, Gods, Demon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1.
[91]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n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pp.78-79.
[92] Richard L. Zettler and Lee Horne, Treasures from the Royal Tombs of U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1998: 94, 95.
[93] Muzahim Mahmoud Hussein, Nimrud: The Queens' tomb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16: 138-140.
[94] Jonathan Mark Kenoyer,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pp.123.
[95] Richard L. Zettler and Lee Horne, Treasures from the Royal Tombs of U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1998: 94-95; Jonathan Mark Kenoyer,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60-162.
[96] 同[92]
[97] 德国柏林佩加蒙博物馆展出的乌鲁克发掘文物。
[98] 卢浮宫展出的苏萨发掘文物。
[99] Charles Higham, Early Culture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River Books, 2002:217-219.
[100] 同[99]
[101] P.R.S Moorey, Ancient Mesopotam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1999:63-71.
[102] 德国柏林佩加蒙博物馆展出的伊拉克北部中亚述时期发掘文物。
[103] Muzahim Mahmoud Hussein, Nimrud: The Queens' tombs, pp.138-140.
[104] P.R.S Moorey, Ancient Mesopotam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pp.85-92.
[105] Jonathan Mark Kenoyer,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6]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埃及馆展出El-Lahun的8号墓出土古埃及第12王朝珠饰。
[107] Richard L. Zettler and Lee Home, Treasures from the Royal Tombs of U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1998:94-95.
[108] Muzahim Mahmoud Hussein, Nimrud: The Queens\' tombs, pp.138-140.
[109]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展出柴胡达罗玛瑙珠饰作坊遗址出土红玉髓珠饰。
[110] Leonard Woolley, Ur Excavation Vol.IV: The Early Periods, University Museum of Pennsylvania, 1955: 7.
[111] The Metropolitan of Art: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edited by Joan Aruz,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3:143.
[112] John Haywood, The Penguin Historical Atlas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enguin Books, 2005: 24-27.
[113] James W. Lankton, A Bead Timeline, pp.62, 69.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编,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88-205页。编辑推文时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